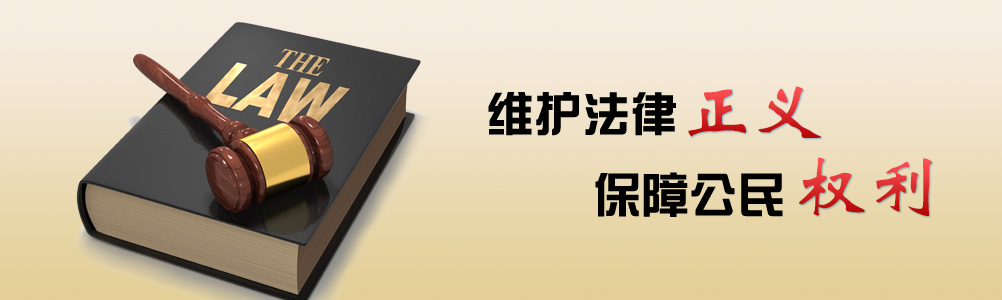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探究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理论上称之为转化型抢劫罪或准抢劫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标准却并不统一。本文旨在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标准作一些研究,以期对统一该罪的裁判标准做一些有益探索。
一、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
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此为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对这一点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无异议,有异议的是行为人先行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是否达到构成犯罪程度,即是否要求先行行为以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为前提(具体而言即是否要求“数额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转化犯只能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违法行为不能转化为犯罪行为,先行行为必需达到犯罪程度,即先构成犯罪才有向抢劫罪转化的可能;另一种观点认为,先行行为无需达到犯罪程度即已具备向抢劫罪转化的前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转化型抢劫罪仅是两种行为的结合而并非两种罪的结合,结合我国刑法有关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规定及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当行为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时,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已经由对财产的侵害转化成对财产和人身的双重侵害(这和典型的抢劫罪所侵犯的客体并无不同),正如抢劫罪不要求“数额较大”一样,转化型抢劫罪也不需要“数额较大”的标准或者先行行为必需要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关于是否要求必需具备“数额较大”这一要素问题,我们可以从“两高”的批复中得到印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8年3月16日《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指1979年刑法,现行刑法为269条),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处罚;如果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该批复的精神与97刑法有关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宗旨完全吻合应继续成为司法工作人员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南和尺度,而不可摒弃现行法律规定而擅自另立认定标准。
二、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客观条件。
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是转化型抢劫罪的客观条件。具体可以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
1、 “当场”的认定标准?
在具体判断转化型抢劫罪的时空条件时,对何为“当场”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场”就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犯罪的现场;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场”就是指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有关的地方。从时间上看,可以是盗窃等行为实施时或刚实施完不久,也可以是数天、数月后;从地点上看,可以是盗窃等的犯罪地,也可以是离开盗窃等犯罪地途中,还可以是行为人的住所等地;第三种观点认为,“当场”一指实施盗窃等犯罪的现场,二指以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一定空间范围,此外只要犯罪分子尚未摆脱监视者力所能及的范围,都属于“当场”。第四种观点认为,“当场”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或者刚一逃离现场即被人发现和追捕的过程中,可以视为现场的延伸。
笔者赞同第四种观点。因为第一种观点对“当场”的理解过于机械,使其时空范围过于窄狭,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实际情况和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利于打击这类犯罪。第二、三种观点把“当场”视为可以完全脱离先行盗窃等行为实施的时空的场所,割断了与先行盗窃等行为的联系,失之宽泛,既不符合该条的立法原意,也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的要求,会扩大打击面。而第四种观点则避免了这两方面的缺陷,因而具有较大的可取性。对于这个问题,大陆法系有一种叫做机会延长的理论,可供我们借鉴。它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暴力与胁迫必须在前行为的机会中实现。所谓机会一是指前行为的现场以及与该现场相连的追捕过程中,原则上要求在时间与场所上与前行为密切相连,但是如果在时间与场所上有一定距离,如果仍处于追赶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则认为是前行为现场的延长,也即机会的延长。判断是否处在前行为机会中,有四个标准:一是场所的连接性,二是时间的连续性,三是与盗窃等事实的关联性,四是追赶事态的继续性。在很短时间内循途抓捕的,则行为人构成抢劫罪。但若被害人隔了较长时间才发现,然后循途追赶,则不具备时间上的连续性,不能算是机会的延长,也就无事后抢劫一说。当然,关于时间“很短”、“较长”的判断标准应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分析。事后抢劫之所以要求暴力、胁迫与盗窃等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是因为转化型抢劫罪与典型抢劫罪属于同一性质的犯罪,必须能够将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胁迫评价为夺取财物的手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暴力、胁迫是在盗窃等行为之后,或者放弃盗窃等犯罪后很短时间内实施的,使得在社会观念上(不是在刑法上)认为盗窃行为还没有终了。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中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才能视为与典型抢劫罪具有相同性质的事后抢劫。如果在相隔很远的时间和场所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则不成其为事后抢劫。具体地说就是本罪的后行的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行为与先前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应具有连续性、关联性、不间断性,即在时间上是不间断的,在空间上是连续的。
2、何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转化型抢劫罪的行为条件必须是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笔者认为其涵义应与典型的抢劫罪中的暴力与胁迫行为作同样的理解。典型抢劫罪的暴力必须针对人实施,并且要求暴力手段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但作为转化型抢劫罪手段的暴力、胁迫是否也必须达到这种程度呢?这在理论上是有争论的。学者们大多认为,本罪同典型抢劫罪有相同程度的危险性和反社会性,尽管暴力、胁迫与夺取财物的时间先后顺序有所不同,但罪质相同,因此,暴力、胁迫的程度也应相同。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本罪大多是在已经取得财物时实施暴力、胁迫手段,就能达到目的,因而,本罪的暴力、胁迫的程度可以轻于典型抢劫罪。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如果已被人发现而抓捕时,为了逃走总会实施一定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论暴力程度轻重与否,一概以事后抢劫论罪,特别是在出现致人伤害的后果时,更要按法定刑很重的抢劫伤人定罪处罚,这就势必造成处罚过苛的不良后果。正因为如此,日本近来的判例对本罪的暴力程度有从严掌握的倾向。笔者认为,“转化型抢劫”毕竟不同于典型的抢劫罪,其作案动机和主观恶性相对较轻,而且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因此,对其实施的暴力程度应有所限制,暴力、威胁的程度,应当以抓捕人不敢或者不能抓捕为条件。如果没有伤害的意图,只是为了摆脱抓捕,而推推撞撞,可以不认为是使用暴力。
实践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转化型抢劫犯罪中暴力、威胁的对象是否只能针对抓捕人,即行为的对象是否有限制。有意见认为,转化型抢劫中,暴力、威胁的对象只能针对抓捕人。笔者认为,标准、常见的转化型抢劫罪中,暴力、威胁行为一般是针对抓捕人而进行的。但在实践中,犯罪分子为达到窝藏赃物、抗拒抓捕等目的,既可能采取针对抓捕人的直接抗拒、阻碍方式,也可能利用抓捕人对第三人或事物的关爱、顾忌而以对第三人或事物实施侵害相威胁。世事多变,案情无穷,人为地对犯罪对象作狭窄的限制,既无实践依据,也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论构成要件,还可能缩小打击范围,放纵犯罪。所以,转化型抢劫罪中暴力、威胁的对象不应有限制。
三、转化型抢劫罪的主观条件问题。
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这是转化型抢劫罪的主观条件。至于行为人是否实现上述目的,则不妨碍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窝藏赃物”是指犯罪分子为防护已到手的赃物,以免被追回;“抗拒抓捕”是指反抗被害人或其他人的扭送、抓捕;“毁灭罪证”是指将现场作案的罪证予以销毁。
这一条件使转化的抢劫罪与典型的抢劫罪在犯罪性质相当和危害程度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基础上得以区别。如果行为人尚未完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的行为,而是正在实施过程中被人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则是故意内容的转化,即由盗窃、诈骗、抢夺的故意转化为抢劫的故意,属于直接引用刑法263条定罪处罚的情形,则不存在转化问题。如果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不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就不属于适用刑法第269条的情况,构成其它罪名的按照其它罪名定罪处罚。
四、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之争。
典型抢劫罪存在既遂与未遂的区别,一般以“财物是否到手”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但是,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未遂与既遂的区分呢?若存在,那么判断标准如何确定呢?对此,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法本意,转化型抢劫罪一经转化就既遂,根本不存在未遂形态。立法者规定转化型抢劫罪的目的在于严厉惩罚行为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让其犯罪性质从处罚较轻的盗窃、抢夺、诈骗罪转化为处罚较重的抢劫罪。行为人一旦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其转化行为同时完成,犯罪性质立刻转化为抢劫罪既遂。因此,不管前提行为是未遂还是既遂,其转化后抢劫罪都构成既遂。
第二种意见认为,转化型抢劫犯的既遂或是未遂应以其先前行为的既遂或未遂作为判断标准,先前行为既遂,抢劫罪也为既遂,先前行为未遂,则转化后的抢劫罪也是未遂。
第三种意见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判断应考察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目的是否得逞,如果得逞,为抢劫罪既遂,否则为未遂。
第四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若行为人实际取得财物或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应认定为抢劫罪既遂,否则为未遂。
笔者原则上同意第四种意见,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作为抢劫罪的一种,也不例外地存在未遂问题:
从理论层面上分析,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问题和既遂、未遂问题是两个独立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应当分别考虑。在转化型抢劫犯罪的处理过程中,转化的成功与否是第一层次的问题,其解决的是定何罪即定性问题,如果转化成功,则直接定抢劫罪,否则,就按盗窃、抢夺、诈骗这些先前行为定罪;而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未遂是犯罪形态问题,其解决的是转化后的抢劫罪是否具备抢劫罪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的问题,如果具备,为既遂,否则为未遂。
从立法原意上分析,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仅仅是犯罪性质的转化条件,对转化成功后的抢劫罪具体处于哪种犯罪形态、如何量刑等一系问题,该条给出的答案是“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可见,对于犯罪形态、如何量刑等这些犯罪性质之外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立法者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与典型抢劫罪的处理标准相同(既然典型抢劫罪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别,那么转化型抢劫罪也自然存在未遂形态)。因此,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不存在未遂形态、认为应以先前行为的犯罪形态作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判断标准,或者认为应以行为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的目的是否实现作为转化型抢劫罪判断标准的理解都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
综上,转化型抢劫罪也存在犯罪既遂与未遂之别。在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全部案情准确判断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未遂问题,既要定性准确,又要量刑均衡,避免“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的错误倾向,以达求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