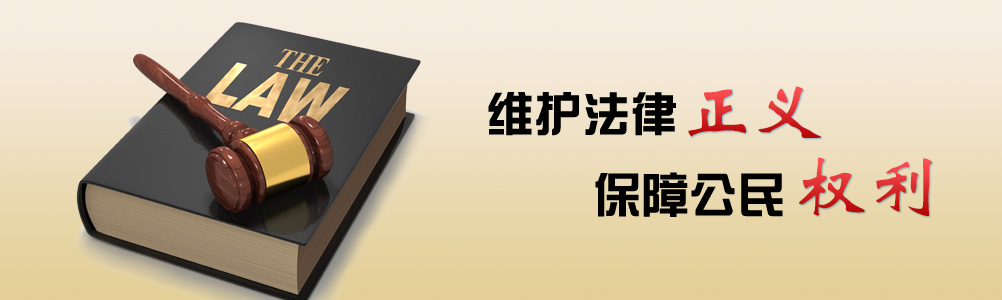“捕诉合一”背景下 辩护人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编者按:2018年11月17日,第二届世君刑事辩护论坛暨江苏师范大学刑事法论坛在江苏师范大学敬文报告厅举办,此次论坛主题为“司法体制变革下的刑事辩护”,专家学者、刑辩律师、司法实务人员共计300余人参加了论坛,围绕当前刑事辩护的热门话题,共同探讨新刑诉法的实施对刑事辩护所产生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樊崇义教授以《刑诉法的修订与刑事辩护》为主题发表演讲;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三庭庭长、天津大学教授戴长林以《三项规程与律师辩护》为主题发表演讲;原中央司法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黄太云教授以《司法改革对刑辩律师执业的影响》为主题发表演讲。
受论坛主办方邀请,江苏圣典(常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常州市律师协会刑委会主任邢辉律师在论坛发表了题为《“捕诉合一”背景下,辩护人如何进行有效辩护》的精彩演讲,邢辉主任结合“捕诉合一”这一司法改革的大背景,立足司法办案实际,站在辩方的立场上,详细分析了辩护人的“三点无奈”之处,并针对出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辩护人进行有效辩护的“五点建议”。以下是邢辉律师出席论坛时发表演讲的内容。
一、一个背景
“捕诉合一”是指一个刑事案件的批捕和审查起诉,由同一部门同一检察官负责。实际上,“捕诉合一”推行后,同一刑事案件的批捕、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将统一交由同一员额检察官统一办理。检察机关在全面推行“捕诉合一”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刑辩律师将面临着新的辩护现实,这一问题不仅体现在审查起诉阶段,而是全面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流程之中,这也促使辩护人在实践中不得不进行新的策略选择和方案安排。
二、三点无奈
随着检察机关“捕诉合一”改革的推行和逐步实施,有律师同行提出,辩护人的辩护空间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辩护的难度会有所上升,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作为刑辩律师,本人认为,辩护人会实际面临着以下“三点无奈”处境。
(一)案件“提前介入”将会大量增多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新《刑事诉讼法》第87条“……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67条“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在捕诉合一与审判中心的司改背景下,“提前介入”将由“破案抓人”向“证据定案”进行逐步转变。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着公安机关主动邀请和检察机关主动提出两种“提前介入”的启动模式,在此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对证据进行全面和有效固定,为检察机关的及时批捕及以后的公诉工作做好充分的铺垫与准备,公安与检察两家司法机关会因此而达成更多“共识”。因此,辩护人的辩护活动不同程度地会受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实际影响。
(二)“二次辩护”将受极大压缩
“捕诉分离”的背景下,辩护人在提请逮捕和审查起诉的不同程序中,可以向同一案件的不同承办检察官提出不同的辩护意见(不予批捕、不被起诉、改变定性等意见)。而在“捕诉合一”的背景下,辩护人虽然同样享有“二次辩护”的权利,但由于案件的承办检察官同为一人,如果前期的辩护意见不被采纳时,辩护人进行再次辩护的意见被采纳的概率无疑会大大降低,辩护人的辩护效果将会被大大压缩,甚至会出现无效辩护的被动局面。
(三)起诉比例将会显著提升
如前所述,批捕检察官由于同时担负着审查起诉的检察职能,鉴于在批捕过程中形成的固定思路和观点,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工作需要,无疑会倾向于将案件移送法院起诉。实际上,承办检察官迫于批捕的压力,在没有出现新的“无罪证据”或者新的“相对不诉证据”的情况下,检察官都会积极作出起诉的决定。
三、五点建议
(一)助推“侦查监督”
传统的“公诉准备”观点认为,“侦查是为公诉做准备的”,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公检法职能分离模式,三机关相互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导致检察机关在事前和事中很难对公安机关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责。但在“捕诉合一”背景下,司法观念急需转变,检察机关无疑会树立“检察引导侦查”的理念,即以批捕、公诉和审判的证据和证明标准去指导、引导和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新《刑事诉讼法》第8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64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捕诉分离”背景下,由于检察机关的办案部门不同,承办检察官不同,很难将“侦查监督”落到实处,而“捕诉合一”背景下,由于案件承办部门和承办检察官同一化,承办人对案件的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比较清楚,从而可以有效避免“侦查监督不力”的实际问题。此外,新《刑事诉讼法》第19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些制度安排和立法规定,无疑会确保检察机关“有能力、有条件、有措施”对公安机关实行强有力的侦查监督职能。
(二)争取“存疑不批捕”
司法实践中,不批准逮捕分为三种情形:绝对不批捕(不构成犯罪);相对不批捕(够罪但无逮捕必要);存疑不批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虽然“批捕”的证据要求不同于“起诉”的证据要求,但在捕诉合一和审判中心的思维模式下,会事实上倒逼检察官对批捕证据控制的更加严格、更加规范和更加细致。辩护人可以充分利用“37天黄金救援期”这一规则,在办案实践中,努力做到“加大会见的力度、加大了解案情的力度、加大取证的力度、加大沟通的力度”,争取获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存疑不批捕的辩护效果。当然,绝对不批捕和相对不批捕也是律师辩护的重要领域,辩护人也不能忽视或者无故放弃。
(三)适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
有人认为,“捕诉合一”会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但这一问题并不需要担忧,主要理由如下:1.羁押必要性审查本身是法定的制度,并不会受到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改革和办案模式改变的实质性的影响。2.检察机关内部设置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考核机制,会给辩护人带来持续的辩护空间。
因此,对于那些“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的案件,如果具备羁押必要性审查规定的“自首、从犯、防卫过当、和解谅解、积极赔偿、未成年人、主观恶性小的初犯、可以适用缓刑”等情节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批捕时间届满一个月的情况下,辩护人应积极向检察机关递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同时提供有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材料,并进行有效沟通,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机会仍然会比较大。
(四)全力争取“不起诉”
司法实践中,不起诉分为三种情形: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检察机关会依法会作出起诉决定,这点无需过多探讨。
1.绝对不起诉。对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符合新《刑事诉讼法》第16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由此可知,从公诉权角度讲,对这类案件,人民检察院或不具有诉权或诉权已经实质消灭。
2.相对不起诉。法律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比如《刑法》总则中规定:领域外犯罪又在外国已经受过刑事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符合自首情形,且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外,《刑法》分则中对于某些特殊罪名的免除处罚也做出了具体规定。比如行贿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罪名中具备特定的条件和情形时,犯罪嫌疑人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有可能适用的“轻罪”不起诉罪名包括:交通肇事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轻伤)、行贿罪、危险驾驶罪、销售假药罪、盗窃罪、挪用资金罪等等。
3.存疑不起诉。又称证据不足的不起诉。主要体现在:证据不充分、证据存疑、证据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等等。对于上述案件,检察机关经两次退查的,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是,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4款之规定决定不起诉的,在发现新的证据时,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重新提起公诉。对此,辩护人仍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审查全案的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这一基本条件,同时还要审查,原存疑不起诉决定书是否经法定程序撤销等案件的程序性问题,以便做好下一步的辩护应对措施。
实践中,绝大部分的不起诉案件,属于“存疑不起诉”,不管是实行“捕诉分离”,还是“捕诉合一”,对于证据可以充分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都是辩护人辩护的重中之重。
(五)力争达成“诉辩交易”
“诉辩交易”,起源于美国司法领域,美国一些联邦和州的地区司法官员采用了以“双方协议”和“赎买交易”的方式取得被告人认罪答辩的司法审判方式。由于诉辩交易的方式简便、易行、快速、灵活、有效地节省了司法办案的成本,因此,在美国有大多数案件是运用“诉辩交易”进行审结的。
2002年4月11日,中国首例“诉辩交易”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辩方放弃“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观点,同意诉方指控的事实、证据及罪名,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同意赔偿被害人因受伤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并要求法院对自己从轻处罚。公诉方同意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请求,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用缓刑。最终,经法庭调解程序,被告人赔偿被害人4万元人民币,法庭对被告人孟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本人认为,“无罪辩护”并非适用于任何案件领域,也并非是最好的辩护,最好的辩护应是“有效辩护”。“有效辩护”旨在通过与有权司法机关协商、抗辩和说服等一系列的活动,最终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争取最有利的司法决定或者裁判结果。任何辩护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化均是辩护人的首选,律师的辩护从来都不能独立于被告人的意志和利益。“诉辩交易”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无罪方面。对于案件存在“硬伤”,证据存在认定的重大争议的案件,辩护人与公诉人协商达成“不起诉”的共识,如果无法达成共识而检察机关起诉的,在审判阶段,仍然可以在法庭的协调和建议之下,双方协商“撤回起诉”事宜,而并非一味地追求“无罪判决”的结果。这里的“诉辩交易”体现在罪与非罪方面。
2.罪轻方面。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辩护人可以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认罚”制度,与公诉人就案件的罪名适用(重罪与轻罪)、法定情节(自首、立功、从犯、防卫过当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据实对被告人进行有利选择)、量刑建议(实刑、缓刑与免刑)等方面力争达成共识,避免不必要的“庭审之上争议”,并力争成果取得法庭的认可。这里的“诉辩交易”体现在重罪与轻罪和刑罚轻重两个方面。
坦诚讲,“疑罪从无”是司法的最高追求,然而现实中的“疑罪从轻”也不在少数,只要能够以最快和最有效的方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和辩护实践一再证明,“认罪讨价还价”本身不失为辩方处理案件时的一种有效策略和方案选择。